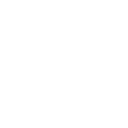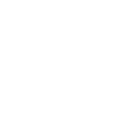u8,u8国际,u8国际官方网站,u8国际网站,u8国际网址,u8国际链接,u8体育,u8体育官网,u8体育网址,u8注册,u8体育网址,u8官方网站,u8体育APP,u8体育登录,u8体育入口

二战后初期日本左翼史学家主导的“战后历史学”将战时日本纳入法西斯主义视角进行批判与反思。但随着日本政治、社会的保守化,右倾学者开始尝试挑战该视角下的史学论说。1976年,伊藤隆提出法西斯主义回避论,绕开日本是否是法西斯主义的讨论,直接宣称法西斯主义一词不具备学术分析效力,提议用革新派论取代法西斯主义论。此后多年左翼学者持续驳斥这种主张,并更新研究方法,以保持法西斯主义论的有效性。论争持续至20世纪80年代末,双方始终未能取得共识。然而,伊藤隆将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与回避法西斯主义的叙事方式强行捆绑,导致此后日本学者过度“慎用”法西斯主义一词,限制了学界对战时日本史的批判性叙述,也扭曲着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这场论争与其说是史学理论之争,不如说是历史认知之争。日本学界的法西斯主义回避论表面标榜“客观中立”,实际上想确立的是一种“去道德审判”的叙事方向,其隐含目的无非是回避法西斯主义一词连带的战争审判和历史追责,进而重塑一种“无罪”的日本历史形象
然而,在这样的国际学术背景下,近些年日本史学界却存在着一个鲜被提及的反常现象,即采用法西斯主义一词进行日本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少。究其缘由,最直接的学术背景可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争。1976年,日本保守主义史学家伊藤隆发文主张法西斯主义一词不适宜用作史学术语,号召在日本史研究中弃用该语。此后,主张日本法西斯主义论说的左翼学者与伊藤隆之间围绕战时日本史研究是否应该使用法西斯主义一词展开论争,持续争辩至20世纪80年代末。论争中,法西斯主义一词在学术领域被缠上了多重争议,导致日本学界从此过度地“慎用”该词。而造成此种状况的深层次因素,其实是战后日本社会在政府引导下日益右倾化、保守化,拒绝对战前历史进行批判的倾向,已深刻影响到学界。回避日本法西斯主义用语的隐含目的无非是回避法西斯主义一词连带的战争审判与历史追责。
伊藤隆力主回避使用法西斯主义一词实质上是历史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日本法西斯主义回避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是通过论证日本非法西斯主义来直接撇清历史责任,而是通过排斥法西斯主义一词,将讨论“日本是否是法西斯”的两方全部污蔑为“非学术”,以此来逃避历史的价值判断。日本法西斯主义这一传统史学共识,没有被日本非法西斯主义的右翼观点瓦解,却被拒绝使用法西斯主义一词的叙述方式冲击,最终促使日本学界形成了一种“日本历史与法西斯主义不相干”的修正主义历史叙事。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学术工具并非某种史学理论或史实依据,而是语言修辞本身。
日本学界虽然有不少针对这场论争的回顾,其中不乏对伊藤隆的批判,但未能基于叙述学视角发现伊藤隆的主张本质上是强制规定了一种修正主义的叙述方式和问题意识;且囿于日本学者自身的学术立场,使得他们普遍对回避法西斯主义的隐性危害认识不够充分。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剖析了日本学界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历史观的变动,也深刻批判了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但目前尚没有以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争为主题的研究。鉴于上述状况,有必要重新审视这场改变日本历史学叙事方向的大事件,警惕其中心人物——伊藤隆在当今日本学术界的“遗毒”。
日本二战战败初期,在美国主导下实施了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其社会一度出现反思战前体制和检讨战争罪行的思想潮流。左翼学者是当时思想界的主导力量。左翼学者将战时日本置于法西斯主义视角下进行深刻批判,构建出完全不同于战前“皇国史观”的“战后历史学”叙事体系。由志贺义雄、守屋典郎等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概念长期被视为战时日本体制的代名词。同一时期自由派学者丸山真男提出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概念则被视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最主要特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法西斯主义作为叙述主语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一直是战时日本史研究的核心论调。
在“战后历史学”的叙述下,日本法西斯主义被理解为明治维新以来天皇制反动体制的延续和升级。藤原彰如此阐释“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垄断资本与天皇制密切结合,强化了对人民的剥夺和统治,同时推进了侵略战争的步伐。以军部、官僚为枢轴的天皇制不仅有绝对主义的特性,而且成为垄断资本对人民实施暴力独裁的机关,是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权力体制。”丸山真男也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充分,资产阶级习惯于向封建权威妥协,因此“明治以来的绝对主义寡头体制可以自然而然地转变为法西斯体制”。这一时期进步学者都认为,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日本近代史的底色始终是反动、反革命的。这就要求战后改革要确立真正的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精神,与战前历史彻底割席。这种认识模式现在常被诟病过于死板,但这种反思和批判,恰恰反映了战后初期进步知识分子的良知。正如日本学者黑泽文贵所说,日本法西斯主义相关论说“归根结底是为了综合地剖析统治阶层对侵略战争的参与程度”。
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开始有意引导国民摆脱“战后”意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愈加重视日本在东亚的战略作用,在经济上对其加以扶植,政治上逐步停止对其战争责任的清算。美国结束对日占领后,日本政界的保守势力更是迅速崛起,1955年“保守合同”的自民党开启了长期执政。经济上日本则借助“特需景气”恢复到战前水平,全社会的心态由战败初期的苦闷转向乐观。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宣告:“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我们正面临着不同的局势。依靠恢复而实现的增长已经结束,今后的增长将依靠现代化。”这段话被视为日本结束“战后复兴”重新迈向现代化的宣言,其中那句“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一时成为了流行语。
随着“战后”意识的消解,将“战前—战后”“历史—现在”作为对立面进行批判叙述的必要性也被相对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质疑“战后历史学”,倡导重新解读昭和史的思想开始冒头,并引发了“昭和史论争”。1956年3月,龟井胜一郎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昭和史》一书的史学方法和问题意识提出诸多质疑。《昭和史》出版于1955年,由远山茂树、藤原彰、今井清一三位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学者合著,发行后十分畅销,被视为“昭和史像的集大成者”。龟井胜一郎的批评引发连锁反应,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等各界学者持续参与到论争当中。龟井等人的批评直指左翼学者的史学方法,认为讲座派学者的研究一味强调经济、阶级关系,“缺乏‘人的视角’”。有学者指出这场论争之所以备受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昭和史》的战时历史书写“与读者自身的时代体验产生违和感,从而引发一些普通读者的质疑”。不久后,吉田裕发表的《日本人的战争观》一书掀起了战记作品热潮,不少知识人开始基于亲历者的“实感”进行历史书写,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延续了战前保守意识的作品问世。
保守主义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就此登场。还是在1956年,“昭和史论争”的参与者之一——文艺评论家竹山道雄,出版了《昭和的精神史》一书。该书强调日本相较于德国、意大利,不存在一国一党体制、集中营、独裁者等要素,因此日本战时体制与法西斯主义体制相去甚远。此后不久,政治学者中村菊男也发表类似言论。中村菊男强调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都是通过大众运动夺取的政权,而日本的政治“始终基于立宪程序,既没有政变也没有大众运动”,因此战时日本不能叫作法西斯主义。在竹山和中村眼中,法西斯主义需要被严格限定为德国、意大利模式,不认可左翼学者将日本视为法西斯主义的论说。在否定日本是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同时,二人还纷纷将批判矛头指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的有罪裁定。竹山道雄指责东京审判从既定结论出发,“歪曲了事实”。中村菊男则着重提及:“印度法官帕尔的‘日本无罪论’熠熠生辉。”可见,竹山、中村等人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暗含着摆脱“战后历史学”的意图,尝试重塑一个“无罪”的新国家形象。
对于竹山等人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当时的主流史学家并没有特别重视。讲座派学者井上清暗讽这些言论算不上历史学研究,指出《昭和的精神史》中存在不少事实错误。但同时他也注意到,“通过巧妙的修辞,虽然未能在理论上说服读者,似乎却在情感上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大约十年后,井上光贞在回顾“昭和史论争”时也评价道:“竹山氏并没有提供理论框架,只是将自己的体验与回忆录视为唯一线索,试图重写昭和史。”因此,竹山、中村等人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可以视为“昭和史论争”当中的一段插曲,是部分非左翼知识分子不满“战后历史学”,重新书写昭和史的一种尝试。但二人并不是专业历史学者,缺乏深刻的理论分析,且言辞中带有过浓的保守政治色彩,因此并没有对学界的主流论说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产生实质性冲击。
即便如此,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中仍有一些论调启发了后来的保守史学家,也为后来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争埋下了引线。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主要呈现三种论调:其一,使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定义。即仅仅把法西斯主义的标准限定在德、意两国,以此将日本排除在法西斯主义范畴之外。其二,采取道德虚无主义的历史观。竹山道雄说:“实际上所谓历史,远远无法满足我们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的要求,是非常残酷的。”暗示对历史进行道德批判是无意义的。其三,利用“近代化论”消解近代日本历史当中的反动、负面属性。竹山道雄如此叙述日本近代史:“明治日本以国家主义为基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功……实际上当时所有有活力的国家都奉行侵略扩张主义,所以日本的罪过只是在于开展得较晚,且推行得过于勉强。至少在当时的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资格对此进行审判。”所谓“近代化论”即是“以西欧为近代化模板,宣扬日本是亚洲唯一实现了近代化的国家”的论说。多年后,安丸良夫指出这种论调在价值观上隐含着“陷阱”:“将生产力发展视为至高价值,相对于这一至高价值来说,军国主义、侵略、压抑民众等问题都只是必要之恶,是附属品而已。”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随着国际和日本国内环境的变化,“战后历史学”构建的批判性近代史叙事开始动摇。历史学研究方法和视角转向多元的同时,部分否认日本战争罪行的右翼保守史观趁机冒头。保守史观之一就是否认战时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一样是法西斯主义国家。由于持这种史观的知识分子完全是政治立场先行,论述逻辑漏洞百出,未能真正撼动“战后历史学”的核心地位。然而,这些保守史观却像沉沙一般暗暗堆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日本学术界泛滥开来。
1968年,佐藤荣作政府以明治建元一百周年为契机举行了“明治百年祭”,并大肆组织官方媒体宣传这一庆典。日本政府盛赞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的经济发展成就,同时感叹现代日本精神荒废,呼唤“传统精神”的再现。借助“明治百年史观”,日本政府向国民传达了一种新的近代史叙述倾向:在过去一百年间日本始终处于“近代化”历程当中,日本最需要的不是反思近代史,反而是回归传统与歌颂历史。“战后历史学”的批评性叙述逐渐受到冷落,自民党政府构建的官方历史叙事最终帮助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学界粉墨登场。
《视角》前半部分从学术角度剖析当时占主流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论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伊藤隆质疑法西斯主义一词并非严谨的学术用语,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定义一直没有定论,尤其是在政治领域该词带有明显的“负面意味”,因此伊藤认为使用该词无法保证学术研究的“中立客观”。其次,他指出既往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论存在不少理论上的矛盾之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讲座派学者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存在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一方面,该论沿用战前“32年纲领”的结论,认为战前日本体制是绝对主义的“天皇制”;另一方面,又将战前日本认定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体制。同年7月,伊藤隆在一场座谈会中详细地质疑了这一点:“所谓绝对主义指的就是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吧”,“如果说是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一直持续了下去的话,哪里还会有法西斯主义兴起的余地呢?”最后,伊藤将日本法西斯主义论的形成原因归结于“远东审判史观”,认为将德、意、日认定为法西斯国家,是美国、苏联等战胜国意识形态引导的,而非严谨的学术讨论。基于以上理由,伊藤隆认为法西斯主义作为学术用语是“无内容”的。他将采取批判立场的历史叙述一律称为“善恶史观”,呼吁在学术研究中将“意识形态”“善恶史观”驱逐出去。
在《视角》的后半部分,伊藤隆提出革新派论,以取代“法西斯主义论”。他指出,在昭和时代,林林总总的政治团体大多有着或激进或渐进、或合法或违法的政治目标,在高压的舆论环境下他们都以“改造”或“革新”自诩。伊藤隆认为在昭和前期,无论是左翼运动还是右翼运动都不能简单地用“进步”或“反动”来概括,他们都有着“打破现状”的倾向,是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一种结果。伊藤隆分析称,以往的法西斯主义论将法西斯等同于“右翼”“独裁”“反动”等负面象征,将法西斯这一研究主体与“大众运动”“近代化”完全对立,这一认识方式过于僵化。由此,他主张采取一种“唯名论”态度,将昭和时期政治团体自我标榜的“革新”这一所谓“中性”词原原本本地用于当代历史书写中,不作任何价值评判。伊藤隆认为,当时以左翼为代表的“进步、革新派”受到打压,而主张复兴传统精神的“复古、革新派”是当时政治的主要推动者,因此应当以这些团体为基轴梳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在革新派论中,伊藤隆不再提及法西斯主义运动,因为一切政治运动都被冠以“革新”之名。当然也不再提及法西斯主义者一词,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革新派”。文章最后伊藤隆强调:“有必要从法西斯主义这一暧昧不明的、易被混淆的用语中走出来。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至40年代前半期世界各国内部面临的诸多困难,与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联系起来探讨,研究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以及此背景下国内诸势力是如何维持政治体制,甚至试图变革政治体制的,他们的尝试最后是如何成功或失败的,应从此种视角出发,重新解读史料,检讨史料。”
《视角》发表的同年8月,小学馆出版了32卷系列丛书《日本的历史》,其中《十五年战争》一卷由伊藤隆主笔,且伊藤隆是丛书中唯一一位非左翼的近代史学者。结果伊藤隆在这段历史中只字未提法西斯主义,反而抛出道德虚无主义历史观,反对就战时日本历史进行审判、追责,声称“战争是国际关系的一种极限状态”,“不能只问‘为什么日本进行了战争’,还要问‘为什么各国都开展了战争’”。针对伊藤隆的论调及史观,松尾章一提出了批评。松尾认为,《十五年战争》一书将法西斯主义时代描述为“梦想遭遇重大挫折的动摇的时代”,这种叙述有拥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嫌疑,指责伊藤隆表面要求“摆脱意识形态史观”,实际上自己却堕入主义、拥护现体制的意识形态。由此,左翼学者与伊藤隆之间开始了论战。
可以看出,伊藤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保守主义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的三种基本论调:狭义的法西斯主义概念界定、道德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以及强调“战时日本史”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近代化论”。但与此前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否定论不同的是,伊藤隆在“日本是不是法西斯国家”这一史实问题上没有停留太久,只是稍稍指出战时日本体制与德国、意大利不同后便调转焦点,将矛头指向了法西斯主义概念以及法西斯主义概念下的左翼史学研究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伊藤隆凭借其扎实的史料功底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将过往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局限强行与法西斯主义概念进行绑定,将一切学术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法西斯主义概念。由此,伊藤隆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回避论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产生了重大冲击。
左翼学者针对伊藤隆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回避论进行了集中批评与回应。1977年12月,《历史学研究》组织了特集“日本法西斯论的再检讨”。杂志编委会在前言中指出,本次讨论致力于“明确日本法西斯研究的视角与课题——对法西斯课题的混乱状况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整理和引导;重新探讨‘日本法西斯主义’概念,并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此处提及的整理法西斯主义概念、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两个主要视角,显然正是为了应对伊藤隆的挑战。
在该期杂志上,安部博纯首先承认伊藤隆所说的法西斯主义概念混乱问题确实存在。不过,安部也指出,这是全世界学术界都面临的问题,而伊藤隆始终没去质疑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仅仅通过质疑日本法西斯主义过往研究就断定“法西斯主义是无内容的用语”,显然并不合理。同时安部也承认,早先“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理论存在矛盾之处,不过这也并非新问题,当前左翼学者早已不再完全因袭“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论”。山口定、西川正雄等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吸收欧洲法西斯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视角也不再局限于“绝对主义”“反动”“保守”等层面,也开始关注到法西斯主义当中“拟似革命”“打破现状”的部分,就此安部认为“‘革新’这一用语固然有效,但它与法西斯主义概念也绝不矛盾”。
左翼学者将伊藤隆回避法西斯主义概念的原因归因于其本人的政治立场。《历史学研究》同期杂志中有一篇作者署名为“壬生史郎”的文章,指出伊藤隆的观点是一种“辨明史观”:仅仅从体制功能的角度出发将“动员国民的能量”“谋求权力的集中”视为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的共同发展趋势,以此试图消解法西斯主义的残酷性和特殊性,这无疑是相对化日本的历史责任。多年后,安部博纯在其专著中也如此评价道:“30年代的右翼相较于法西斯主义更喜欢革新这个词,提议把政治辞典中的法西斯主义一词置换成革新的研究者,其动机本身似乎就出于(新)右翼性质的政治考量和立场。”
此后不久,进步学者在法西斯主义研究方法上又取得较大突破。1979年,山口定发表著作《法西斯主义》,在传统唯物史观和丸山学派基础上开辟了“比较法西斯主义”的新方法。山口提出采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综合比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此外,山口定的另一大贡献是借鉴欧洲法西斯研究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主义判定标准——“同盟理论”。山口认为法西斯体制最重要的标志应该是“既有统治阶层当中的反动部分与所谓拟似革命的势力达成了广义上的政治同盟”。以往唯物史观和丸山真男都强调法西斯主义“反动”“反革命”的属性,而随着实证研究的进展,不少学者发现昭和领导层中不乏迎合所谓“近代化”潮流致力于“打破现状”者,这一点往往成为保守学者否认日本是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理由。山口定的“同盟理论”在此基础上则重新思考了法西斯主义与“近代化”“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一战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面临危机,当时法西斯主义表面上承诺破坏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既有秩序,迎合大众对革命的期待,但实际上法西斯主义始终致力于防范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它既是“拟似革命”的,也是“反动”的。山口在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提供了更为立体的认识角度,使得法西斯主义论和实证研究能够有效结合,因此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领域,日本学者至今仍会参考山口定的“同盟理论”。
《法西斯主义》发布的次年,《历史评论》杂志便组织了“法西斯主义”特集,邀请山口定等学者就当时法西斯主义研究动态进行对谈。对谈中山口凭借自己的新理论再次抨击伊藤隆。他指出,“权威反动与拟似革命的同盟”这一法西斯主义标志与伊藤隆口中的“复古、革新”派是相通的,伊藤隆主张的所谓新视角完全可以纳入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当中。使用法西斯主义术语进行批评性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不冲突。据此,山口质疑伊藤隆坚决回避法西斯主义一词的实际动机是“站在‘实证主义’立场,将主张法西斯主义概念有效的研究视角看作意识形态产物,这不是反而自己先带上了意识形态色彩吗?”
面对左翼学者的批评,伊藤隆作出争辩。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的主张存在意识形态倾向,诡辩自己从未讨论过“法西斯主义实体”,只是主张法西斯主义一词不宜用于学术分析。但对于壬生史郎所说的“将历史责任相对化”的批评,他承认自己确实有这一意图,并坦言“历史研究不应该站在审判‘责任’的立场”。面对山口定等学者在法西斯主义研究理论上的更新,伊藤隆不得不承认山口提出的“拟似革命”与自己口中的“革新右翼”两个概念所指几乎一致,在研究视角上差异并不大。但他依然固执地坚持:“这并不意味着使用法西斯主义概念就会产生益处。”伊藤隆甚至一度稍稍让步说道:如果非要在学术上使用法西斯主义一词的话,那最好抛开意识形态,“严谨地采用一个中立的定义”。
由此可见,在论争中法西斯主义视角摆脱了部分旧理论框架的束缚,与实证研究方法实现结合,其学术性得到了有效延续。伊藤隆也不再执着于批评日本法西斯主义论的视角局限,而是将拒绝使用法西斯主义一词的理由主要归结为保持所谓的“客观中立”。他坚称法西斯主义一词带有含混的“非难”意味,使用该词从事历史研究将陷入道德审判的“善恶史观”。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中,近代日本的治安维持法和特高警察常被批评为“反革命”,伊藤隆则主张,实际上二者的出现是二战期间全世界的“风潮”,没有必要苛责,也不应就此将日本纳入法西斯主义这一特殊意识形态当中。他说:“用一种超历史的‘价值’或‘生活观’来‘批判’与之相悖的日本现实,这种倾向是非历史的认识。”
然而,对于试图破坏“战后历史学”权威地位的伊藤隆来说,“没有共识”本身就堪称一种“胜利”。论争之后,法西斯主义概念在日本学界备受争议,连同“日本是否是法西斯主义”这一讨论也被许多学者搁置起来。“战后历史学”确立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这一史学界共识也随之瓦解。虽然日本学界普遍认识到伊藤隆的言论中带有明显右翼、保守意识,但他倡导的“去道德评判”这一新的“学术”规范,却在论争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追捧。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社会整体的右倾化,左翼学者在学术界影响力减退,日本多数学者倾向将所谓“去价值评判”的实证研究当作“科学”态度,法西斯主义一词在日本学者的近代史叙述当中出现得也越来越少。
酒井哲哉提出伊藤隆的方法具有“偏向”和“生产性”两个侧面。关于“生产性”,酒井认为革新派论至少有三点富有启发性:(1)相较于强调“非理性”“强权压迫”的法西斯体制论,革新派论发现了新体制运动参与者的理性和主体性侧面;(2)新体制运动当中劳动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往常被法西斯主义论忽略,革新派论发掘了这一具有社会史价值的潜在视角;(3)日本法西斯主义论通常只强调“大正民主”到“昭和法西斯”之间的断裂性,“革新派”论则格外关注两个时代之间复杂的连续性。酒井指出,当时海外学术界已经开始将“革新”“疑似革命”等侧面纳入法西斯主义概念进行研究,革新派论的以上视角与20世纪70年代冒头的新左翼学者之间也具有不少共识,如果革新派论能够正视“比较法西斯”研究的最新动向,又或者坚持法西斯主义概念的日本学者能够正确把握革新派论当中“生产性”的部分,论争非但不会“空转”,甚至可能催生更多有意义的成果。不过,酒井最后又不无遗憾地感概:“只是这一可能性,由于伊藤氏本人从一开始就拒绝大正民主、法西斯主义等概念,最终恐怕只能带来一些不完整的成果。”
伊藤隆的新视角有助于拓展战时日本政治史研究,但没有必要回避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相反,这些新视角本来同样可以纳入法西斯主义研究当中。结果伊藤隆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向”,强行在两种论说之间设置了藩篱。这导致后来的年轻学者在从事实证研究时往往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产生先入为主的疏离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采用法西斯主义视角的近代史学者在日本学界急剧减少。到90年代末,伊藤隆的弟子古川隆久甚至一度宣称:日本法西斯主义论成了“只有站在左翼的政治立场才有根据的学说”,“已经失去有效性了”,“朝着自身的方向深化没有意义”。
在论争之后,不少学者受革新派论启发开拓了新的昭和史研究视角和议题。例如,伊藤隆的弟子季武嘉也尝试用“举国一致”这一所谓“中性”概念去理解日本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所进行的政治变革,在“对外危机”与“国内改革”的关系研究上作出了标志性的贡献。古川隆久用“权威主义体制”概括战时日本体制,发现以往被认为在战时受到彻底压制的议会、政党势力其实保有不少“韧性”和自主性,同样拓展了昭和政治史研究。此外,伊藤隆在《视角》一文中还曾简略地提出将来昭和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有必要打破“战前”“战时”“战后”相断绝的固有认知,尤其需要梳理战时的“国民总动员、组织化”与战后民主主义之间的关联性。而这一视角,正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日本兴起的“总体战体制论”的核心关注点。“总体战体制论”发起人之一的山之内靖表示,他虽然不完全排斥法西斯主义一词,但相较于法西斯体制论强调战时的“非理性”“反现代化”一面,他更强调战时日本社会的“再组织”实现了某种现代化机能——“强制的均质化”,而这一机能最终延续到了战后民主社会。
与此同时,以上回避法西斯主义概念的学者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去价值判断”的观点,他们在研究视角上普遍存在价值观混乱、对战时日本史缺乏深刻反思等问题。例如,古川隆久便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明显的不信任。近年古川在悼念伊藤隆的文章中还说道:“伊藤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于说明历史没有帮助。”又如,“总体战体制论”单纯将“强制的均质化”这一社会机能视为“现代化”的标志,一味强调“战时”与“战后”的连续性,也导致“淡化了战争以及法西斯主义惨祸”。
在经历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争后,如今相当一部分日本学院派学者的学术取向表现为:只在所谓实证上一味“求真”,而忽视“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与历史认识”等社会职责。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争后伊藤隆史观所遗留的负面影响。正如近些年黑泽文贵对日本学界现状的思考:“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研究者,有着和伊藤隆一样的想法……其中一面就是对价值判断的学问表现出‘禁欲’的特征。”“比起先验的‘恶’这一价值判断,他们认为明确政策的决定过程和实施过程以及体系的运作方式是更为必要的。”但与此同时,黑泽文贵也提醒到:“探究历史事实的研究姿态并不意味着必然与‘政治性’或‘价值判断’无关。不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史观,在实证研究中采取何种视角,将何者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选择本身就是带有某种政治性或价值判断的,这一点不言而喻。”
她指出在论争后,那些非日本法西斯主义论视角所开创的议题同样可以纳入日本法西斯主义论视角下,并且能够为历史研究带来新的反思。例如,伊藤隆、古川隆久、“总体战体制论”者都强调战时日本体制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大众的“变革”“解放”要求,民众在战时日本体制下拥有相当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沿着这一视角左翼学者吉见义明洞见了“法西斯主义”当中“拟似革命的大众运动”的重要性,提出“草根的天皇制德谟克拉西”概念,由此引出了反思民众战争责任的新问题意识。
尽管伊藤隆一再声称要避免学术被政治意识形态左右,但在战时历史的讨论上一味回避使用法西斯主义等批判性词汇,必然限制学术研究的价值导向,从而陷入另一种“意识形态先行”的困境。2015年,中国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日本国内某些右翼学术团体便借机大放厥词,污蔑中国将“抗日战争”等同于“反法西斯战争”,是对日本发动“历史战”。这些右翼学者在学术上援引的主要依据之一,便是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争期间伊藤隆早已说明日本历史不适用法西斯主义概念。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倡议今后进一步“细化”伊藤隆的主张。可见历史学者拒绝法西斯主义等批评性术语所产生的影响绝非仅停留在“语言叙述”层面,而是深刻地影响了大众的“历史认识”。右翼学者俨然已经将“不使用法西斯主义概念”等同于日本非法西斯主义,并将日本学界这种历史叙事倾向当作了某种“学术共识”。
立足当代历史研究,应该意识到伊藤隆借助概念和史学方法的讨论,将某种政治立场隐藏在了语言修辞之中,并且至今都在制约着日本思想界的历史反思精神、责任意识。我国学者赵轶峰在回顾当代日本学界的史学认识时特别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的历史修正主义一度盛行,而这其中“所谓历史学‘语言学转向’的言说在这种语境中具有比在其他语境中更明显的相关性”。伊藤隆身上虽然没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家色彩,但其日本法西斯主义回避论无疑正是一种借助“语言叙述”诡计达成的历史修正主义论调。
日本战后初期左翼史学家主导的“战后历史学”将战时日本纳入法西斯主义阵营展开批判和反思叙述。但随着日本政治、社会的保守化,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否定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企图重塑一个“无罪”的国家形象。他们的尝试并未能动摇日本法西斯主义论的主流地位。尽管如此,在日本政府引导下,上述保守史观与严肃的学术研究逐渐交融,20世纪70年代后期修正主义史学家开始将争点从史实层面移开,转而在叙述层面解构“战后历史学”。
1976年伊藤隆提出日本法西斯主义回避论,绕开了关于“日本是否是法西斯主义”的讨论,直接宣称法西斯主义不能充当学术分析用语。除此之外,伊藤隆提供了自己的研究视角——革新派论,以取代日本法西斯主义论。左翼学者对伊藤隆的挑战予以回击,并更新研究方法保持日本法西斯主义概念的有效性。面对左翼学者的回应,伊藤隆又转而将核心争点放在了历史叙述能否带有价值判断的问题上,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未能取得共识。20世纪80年代末,论争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逐渐趋于平息。两大论说在实证研究领域虽然得以各自发展,但随着日本社会整体的右倾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接纳“去价值判断”的历史叙述方式。法西斯主义一词连同左翼学者的批判视角在日本学界逐渐失去主流地位。
日本学界的法西斯主义回避论表面标榜所谓“客观中立”,实际上确立的是一种“去道德判断”的叙事方法,进而在事实上重塑一种“无罪”的日本历史形象。由于伊藤隆强行将法西斯主义等批判性概念置于“实证方法”“新视角”的对立面,使得后来的学者在接受新视角与实证研究方法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对批判性历史叙述产生质疑。论争之后,日本学界兴起了优先考察历史过程,却避免对历史进行任何价值判断的所谓“实证”潮流。这种将实证研究方法与“去价值判断”叙事方式强行绑定的史学研究倾向,至今仍在日本学界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客观上严重束缚着日本学界对战时历史的反思意识。
然而,从学术史角度回顾这场论争不难发现,伊藤隆虽然在日本近代史实证研究领域提供了不少有效视角与新课题,但这些新视角本身与法西斯主义概念并不冲突,甚至可以为历史批判带来新的问题意识。伊藤隆的革新派论的合理性并不能构成回避法西斯主义一词的充分理由。在战时日本史研究中回避法西斯主义一词既无必要,也不应该。这种偏狭的历史叙事方法只会助长日本思想界放弃历史反思、逃避历史责任的倾向,成为右翼分子的舆论工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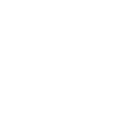
@HASHKFK